在阜阳颍州的晨光里,铁皮桶中静卧的面团,正悄然醒着,像一首未启封的民谣,等待被沸水唤醒。那是付家吃吃看格拉条的清晨——五点半,天光未明,街角已排起长队。人们不语,却心照不宣:这一天,若没吃上一碗格拉条,便不算真正开始。
格拉条,这三个字在皖北的方言里,不只是面食的名称,更是一种乡音的回响,是土地与汗水揉捏出的倔强。它不似江南细面那般婉约,也不似北方面条那般豪放,它有自己的脾气——筋道、粗犷、香浓,像极了这片黄土地上的人:朴实中藏着热烈,粗粝里透着深情。
当面团被压入“漏床”,那一瞬,仿佛撞见了星空倾泻。银白的孔洞下,金黄的面线如流星坠入沸水翻腾的江湖,沉浮、舒展、定型。那不是简单的煮面,而是一场仪式:水是江湖,面是命运,火候是宿命的推手。煮得恰到好处的格拉条,根根挺拔,曲线倔强,不软不烂,咬下去“吱呀”作响,是生命在齿间回响。
捞出,沥水,入碗。一勺浓稠如墨的芝麻酱泼下,瞬间裹住每一寸筋骨。那香,是岁月沉淀的醇厚,是石磨碾过千粒芝麻的低语。再撒上清脆的豆芽,如撑起一片脆亮的月光,最后,一把荆芥叶轻轻覆上——那是灵魂的点睛之笔。荆芥的清香,不张扬,却执拗地在唇齿间弥漫,像童年巷口那阵突然袭来的风,带着泥土与露水的气息,让人蓦然怔住:原来,乡愁真的有味道。

我曾在一天早晨走进付家吃吃看格拉条店。窗外雨丝如织,屋内热气蒸腾。粗瓷大碗捧在手心,芝麻香升腾而起,竟将黄昏熨得平展,仿佛岁月的报纸,一页页摊开,印着旧日街巷、灶台、童年踮脚看锅的影子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:为何央视镜头屡屡对准这间不起眼的快餐店——它卖的从不只是面,而是两代人对“地道”的执念,是对“阜阳味”的集体记忆。
每天从清晨五点到午后三点,食客络绎不绝。有赶早班的工人,有专程驱车而来的游子,也有举着手机直播的外地食客。他们或许不懂“漏床”为何物,也不知“荆芥”学名叫什么,但他们知道:这一碗,是阜阳的魂,是吃一口就忘不掉的乡愁。
付家的格拉条,从来不是一道小吃,它是游子与故土之间,最柔软也最坚韧的脐带。
一碗面,能有多重?在付家,它重过千言万语,重过岁月山河。它让漂泊的人知道:无论走多远,总有一碗面,在等你回家。(傅友君/文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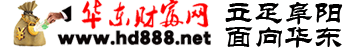




支付宝转账赞助
支付宝扫一扫赞助
微信转账赞助
微信扫一扫赞助